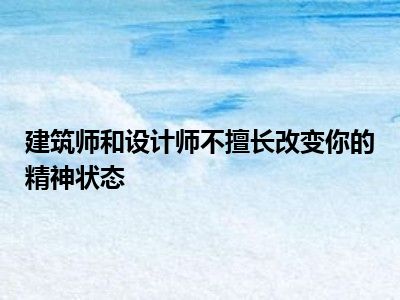
欧文哈特利(Owen Hatherley)在观点专栏中说,通过她的最新展览,英国艺术家劳拉奥尔德菲尔德福特(Laura oldfield Ford)比任何建筑师或设计师都更有可能改变你对伦敦工人阶级景观的理解。
在劳拉奥德菲尔德福特的展览结束时,它位于伦敦市中心西北的里森格罗夫的展厅。这些图片取自该地区最新建筑的房地产宣传册。
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内部视图。虽然房间很小,但是家具很贵,而且视图试图隐藏这个事实。朦胧的现代主义灯椅、豪华的沙发、摆放着设计书籍和艺术品相框的茶几。你可以通过落地窗看到这些东西——如果你只是在这一地区闲逛,你会注意到这是约翰索恩爵士的三位一体玛利莱波恩教堂(Trinity Marylebone,我们将通过“传教士教派”(Missionary Sect)学习)的尖顶所标志的位置的鸟瞰图。
在这个干净的线条空间的角之间,sc草有着五彩的字迹,颜色被着色了,看起来很诡异,有放射性。这里发生的是一场魔术表演,试图抹去这个完美高层售楼处的形象。这些无处不在的照片和平庸的超现代性,暗示着所有最终消失的被遗忘的瞬间、殷切的希望和失去的联系,虽然短暂地过去了,却又被重新带回了人们的视线。
在过去的十年里,奥德菲尔德福特一直试图维持一个鲜为人知的伦敦。
在过去的10年里,奥德菲尔德福特一直试图通过他的画家和画家的作品来维持伦敦很少有人记得的深蹲、市政厅和警戒线的存在。作家,尤其是在她的杂志《野蛮的弥赛亚》(野蛮的弥赛亚)里,2011年被Verso收进了一本书里,以防它预期的骚动。
055-79000平均发表伦敦的具体部分,如韦斯特威,国王十字,斯特拉特福德,希思罗机场等。并以拼贴、书写或打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包括她自己和其他人。包括扭曲的照片,物业效果图,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她自己的密集扭曲的倒影,通常在比罗岛上被仔细遮蔽,到处都是废弃的工业遗址,破旧的维多利亚式寮屋,工业区,英雄的混凝土工程,以及GLC houses迷宫般的人行道和庇护庄园(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对于规划师和建筑师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很难巡逻,而且,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它将包括20世纪80年代濒临灭绝的亚文化部落,包括无政府朋克、光头党和粗鲁男孩,
那些认为一切都很美好的人,很容易讽刺多愁善感这种东西。然而,在《野蛮的弥赛亚》中,不仅仅是当富人被限制在梅菲尔-贝尔格莱维亚-肯辛顿的飞地,他们的家人住在瑟贝顿而不是佩卡姆时,伦敦有多伟大。她的幽灵人物没有做到的是把伦敦变成一个新城市,一个没有多少工作和微不足道的财产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到处走。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于是在她的拼贴画中,他们代替了21世纪的伦敦。但现在也能找到它们——这本杂志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记录它们。
这是一个身临其境的环境——这个野蛮的狂热分子将最接近建筑。
Alpha/Isis/Eden(以当地三座面临拆迁威胁的高层建筑命名)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早期的展览往往是绘画和素描,但这是一个沉浸式的环境——这种野蛮的狂热和理性城市规划的坚定反对者将最接近建筑。这是一个理想的位置,伦敦市中心的无冕部分。
该地区的大部分都非常富有(早期的建筑反应——托尼弗雷顿早期的优雅和柏拉图式的严谨的李森画廊——提醒了艺术在这种转变中的作用),但19世纪70年代至70年代建造的市政厅和皮博迪所有权房屋的高密度意味着仍然没有工人阶级大都市生活的迹象——咖啡馆、自助洗衣店和简单的街头市场。
陈列室的入口处贴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可以沿着埃尔金街的蹲坑,沿着威斯特威地下的酸屋党的路径。废弃金属堆中出现的奇怪建筑.阿克拉姆大厅,梦想和流浪的黄昏世界”。在内部,一楼变成了房地产广告、房地产的图纸和快照、地下通道和附近的马里波恩立交桥的拼贴画,上面布满了文字,有时加密,有时突然变得清晰。我的奴才们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金属格栅门,用来防止蹲着,用来放这些。原文为免责声明“生活方式图片仅供参考”。
最引人注目的是声音——杰克莱瑟姆的一小时音乐创作,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野蛮的弥赛亚》。结果是迷幻的,她的阅读蒙太奇,豪华公寓营销模式的片段,周围街道的声音,无人机的嗡嗡声和他专辑《果酱城》中展示的令人眩晕的电子灵魂。
走了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一样了。
经过一段时间(这需要时间),在这个空间里,声音和图像融合在一起。奥德菲尔德福特柔和的西约克郡色调与山川之间倾斜但暴力的文字形成鲜明对比。一路向西;森格林曼德姆;伦敦被唤醒了。所有这些休眠的隐藏货币都暴露了出来。
你走了之后,会发现你的处境完全不一样了,你的心理地形发生了变化和过滤,以至于“心理地理”写作这种传统的文化隐喻已经做不下去了。
建筑师和设计师不擅长这个。它在过去意味着“语境”和“参照”,政治是“协商”,现代主义成为对事物的肯定。这样就压制了巨大的压力——那些你本不打算考虑的事情,以免让抽象变得复杂,或者暗示抽象本身从根本上就是腐败的。
Alpha/Isis/Eden所涉及的一切,连宣称的“激进”的架构实践都无法使用。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它营造了一个充满愤怒、记忆、渴望、复仇和团结的环境,这个城市在努力把这些情绪和压抑这些情绪的人挡在外面。